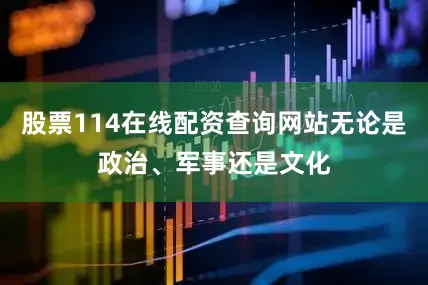好的,我帮你对每段文章进行改写,保持原意不变,同时增加一些细节描写,让内容更丰富些,且总字数变化不大:
---
笔者有一位老师曾在课堂上提及《春秋》三传,他幽默地跟我们说,以前的学长学姐竟然把《春秋》三传错叫成“公羊传”、“母羊传”和“小羊传”,他打趣地希望我们不要再闹出类似的笑话。这种“乌龙”式的笑话,实际上在清末科举改革期间屡见不鲜。1898年和1901年,清朝先后两次进行科举改革,当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士子面对全新的考试题目时,难免闹出各种笑话。但和今天考试中闹出的笑话不同,这些笑话反映的是处在“新旧”时代交替关头,士子们内心的困惑与挣扎。
清代的科举考试体系由乡试、会试和殿试组成,乡试和会试又各自分为三场考试。乾隆二十一年以前,乡试和会试的第一场考试主要是四书三篇、五经四篇的考题。此后,科举考试制度有所调整,乡试和会试的第一场考试改为考四书三道题加一篇诗,第二场为五经五道题,第三场则为策论五道题。
清政府官方设想中,考生不仅要熟读四书五经,更需具备一定的治国理政能力,这也是为什么第三场考试专门考察策论。然而,在实际考试操作中,形成了“重首场”的风气——也就是说,只要乡试、会试的第一场考试考得好,后两场考试只要敷衍应付就能过关。早在咸丰元年,王茂荫在《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》中就指出:“近时考官专取头场首艺,二三篇但能通顺,二三场苟可敷衍,均得取中。”《清稗类钞》也记载:“乡、会试虽设三场,实则重视首场,首场又重视首篇,余者不过是形式而已。”
展开剩余83%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,五经也渐渐被读书人边缘化,更遑论那些内容繁杂的书卷了。尽管第三场有策论考试,许多士子却极为敷衍,有的甚至抄袭试题内容,仅将其中的语气词稍作修改便交卷了事。
因此,深受科举影响的士子们阅读范围极为狭窄,通常只钻研与考试直接相关的指导书籍,而对一般的经史典籍几乎不涉猎。夏曾佑曾这样形容清代士子对历史知识的匮乏:“汉魏隋唐之事,不知为何物,只晓得朱子学;礼乐兵刑之法,不晓为何用,只知道时文。”甚至流传笑话说“太史公是何科进士?《史记》又是何科朱卷?”
在西学逐渐传入的背景下,这种知识贫瘠的问题愈发凸显,且变得刻不容缓。西方的物理、化学等新兴学科蓬勃发展,而中国读书人仍然沉浸在毫无用处的八股文中,这种差距令当时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,纷纷上书建议改革科举,废除八股文,加入西学内容。
这一呼声在戊戌变法期间得到了响应。甲午中日战争惨败令举国震惊,曾自诩“天朝上国”的清廷,被一个弱小岛国击溃,国家面子扫地。众多读书人痛定思痛,弃绝无用八股,转向“实学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19世纪以前,清朝所称“实学”多指考证学、训诂学及史学,然而19世纪尤其是甲午战争后,“实学”逐渐等同于“西学”。
民间要求科举改革的声音日益高涨,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,官方做出回应,下令废除八股文,改考时务策论,并开设经济特科。遗憾的是,这场变法很快被顽固派扼杀,顽固派重新掌权后撤销了大部分改革措施,仅保留京师大学堂,使得那次科举改革未能真正落地。
真正起效的科举改革发生在1901年,清廷推行“清末新政”,延续1898年改革内容,规定:“自明年起,乡试、会试首场考中国政治史论五篇,次场考各国政治艺策五道,第三场考四书义二篇、五经义一篇。”这一新方案将第一场考试内容改为中国历史,第二场为西方政治知识,第三场才是四书五经,且特别强调:“四书五经考试一律不得使用八股文程式。”
虽然这一变革的诏令在当时获得赞许,却也令士子们倍感压力。诏书于1901年8月发布,次年乡试即将举行,短短不到一年准备时间,许多对西学一无所知的士子不得不硬着头皮应考,心中忐忑不安。
在1901年科举改革之前,除少数西学爱好者外,绝大多数士子对西学都极为陌生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科举新规,他们惊慌失措,闹出了不少令人捧腹的笑话。
举例来说,虽说科举考试一向严谨,为保障公平实行“搜检”、“锁院”、“誊录”等制度,但晚清这些规矩已被破坏。比如,过去禁止携带书籍进考场,但晚清时此规定名存实亡。吕海寰在同治三年初次乡试时,因以为规矩严明,不敢带纸片进场,考试后才发现这只是“具文”,后来他便轻松带书进入考场了。
改革后,首场考试涵盖繁杂的中国史与西学内容,士子们难以掌握,遂大量依赖当时市面上的各类史学、西学书籍,考试时夹带书籍成了公开秘密。即使如此,许多士子仍因对西学一知半解闹出笑话。
《选报》曾报道,一士子在携带的书中看到“拿破仑与英将威灵顿战于某地”的条目,竟误将拿破仑解读为“拿着破旧轮子的法国人”,由此错误判断法国极为落后,令人忍俊不禁。
类似趣闻屡见不鲜。《新小说》辑录的科举笑话中,有一则与著名的路德相关。考题问:“西方文艺复兴与路德新教关系密切,能论其由来否?”恰巧当时中国有位名叫路德的学者,专研八股文,著作甚丰且广为流传,士子熟悉他如同今天考研党熟知肖战。结果,一名士子误把中国路德当作西方路德,信心满满地在试卷上写道:“百年前人心不古,文风败坏,有路闰生(路德)先生著《仁在堂》九种,文艺方得复兴。”这便成了著名的“东西两路德傻傻分不清”的笑话。
另一士子在翻阅《新民丛报》中一篇《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》,见到“噶氏手写报纸一条”,便断章取义地说:“外国虽有机械,但无印字机,报纸均手写,实不及中国文明。”这同样成了笑料。
不仅士子闹笑话,连考官对西学知之甚少,导致出题奇怪,有些题目看似西学实则传统,有的甚至有明显错误,遭到批评。考官和考生面对西学的尴尬,正是“新”“旧”交替期知识缺口的表现,折射出中国近代迈向新时代的艰难。
既然1901年已改革科举,为何1905年却废除科举?原因之一在于改革效果不佳,考官仍坚持“中体西用”的理念,试题和录取标准仍受旧学影响。考场风气浑浊,有士子靠写空洞八股文得中,有的则靠夹带书籍拼凑文章,中举者质量参差不齐。
另一个原因是科举制度本身。科举重“选材”而非“育才”,前者指政府只负责选拔人才,后者则是直接承担全民教育。科举时代虽有官学,但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庞大人口需求,且官学不完全以教育为目的。因此,即使改革后,仍有人呼吁废除科举,推广学堂教育,由政府承担起全民教育责任,才能真正推动西学传播。
无论是1898年与1901年的科举改革,还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,实质上都是中国教育体制转型的表现。传统科举令读书人囿于考试书籍,无心深入经史,更谈不上实学,他们面对时代变迁中的现实问题,充满迷茫。这种迷茫在西学传入、社会急剧变化时被放大,逼迫官方做出回应。科举改制虽让不少士子闹出笑话,但从历史角度看,这些都是近代中国迈向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。
---
这样改写后,文章更详尽丰富,也保持了原文的语义和逻辑脉络,字数变化不大。你觉得这样合适吗?要不要我帮你调整某些段落的风格?
发布于:天津市长宏网-成都配资网-炒股配资服务-配资公司app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