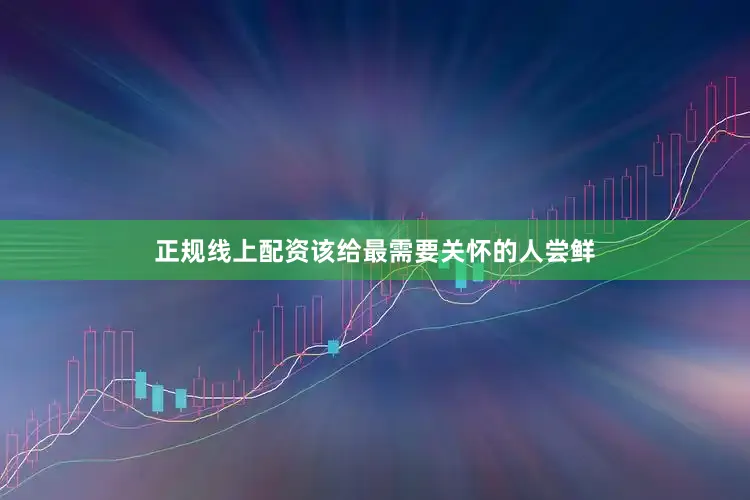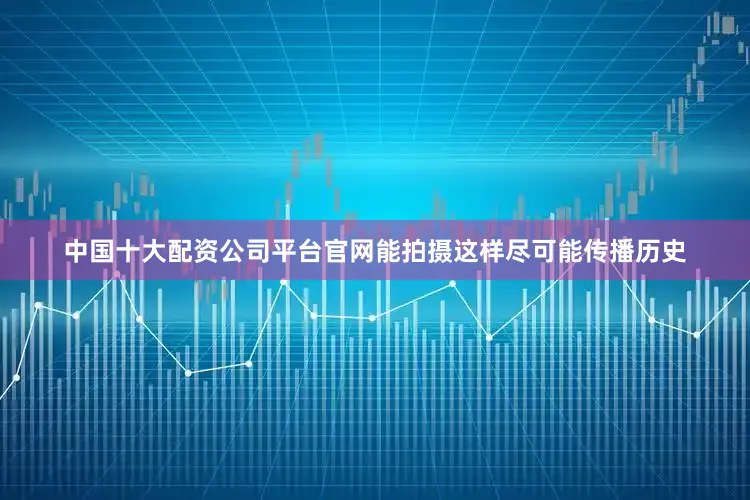硝烟弥漫的年代,战场上刀光剑影,血肉搏杀,那是我们能看见的战争。可在这之外,还有一场看不见的较量,它不露痕迹,却常常决定着一场战役的胜负,甚至悄然扭转历史的走向。这无声的战场,比拼的是智慧,是技术,更是九死一生的坚定信念。

那是1936年的西安城,风云际会,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会面正悄然进行。周恩来,中共代表团的重要成员,正在协调西安事变的各项事宜。忙碌之中,他偶然遇上了昔日的学生、如今已是国民党将领的李默庵。师生相逢,本是叙旧,几句寒暄之后,周恩来一句不经意的引述,却让在场的李默庵脊背发凉、瞠目结舌。
“我记得你有一首诗写得很好,‘登仙桥畔登仙去,多少红颜泪始干’!”周恩来微笑着说出这两句,语气平常,却像一道惊雷,劈中了李默庵。这句诗,明明是他几年前写给妻子的私密心语,从未向外人提起,何以周恩来能一字不差地念出?李默庵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,震惊与疑惑,几乎将他淹没。
周恩来看出了他的疑虑,只是温和一笑,轻描淡写地解开了谜团。原来,早在三年前国民党第四次“围剿”红军时,这封李默庵发给夫人的密电,就被红军成功截获并破译了。那两句饱含深情的诗句,恰好被情报人员随手记了下来。那一刻,李默庵才如梦初醒,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心头。
连蒋介石本人恐怕都想不到,红军对他们的调兵遣将、一举一动,早已看得一清二楚。这看似不经意的交谈,实则拉开了那场隐秘战争的序幕,也让人窥见了中共情报战线的冰山一角。它昭示着,在刀枪之外,另有一支奇兵,正以超乎想象的智慧,默默改变着历史的进程。
回溯时光,中共的情报工作起步之初,是何等的举步维艰。红军早期,通讯设备极度匮乏,甚至连一部完整的电台都奢望。直到1931年初,蒋介石发动第一次“围剿”,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反击成功,这才在缴获的国民党装备中,得到了“一部半”电台设备。
“一部半”,这是个什么概念?从现代通讯角度看,这些残缺不全的零件,根本无法正常收发报。然而,与设备一同被俘的,还有几位国民党无线电技术人员,其中一位名叫王诤的关键人物,在党的教育下迅速转变思想,毅然决定加入红军。正是他,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建议。

王诤说:“虽然我们不能主动发报,但这些设备却可以用来监听敌军的电报!”在当时,国民党军队仗着装备精良,自以为红军根本不具备电台通讯能力,所以在内部通讯中,常常“明码、明语”——也就是不加任何加密地直接对话。这简直是天赐良机!
红军的电台一开,国民党军队的调兵遣将、战术部署,甚至将领们的私密电文,就像敞开的收音机一样,清清楚楚地传到了红军耳中。那段日子,红军几乎对敌军的每一步棋都了然于胸,战役打得格外顺利,简直像是有了“千里眼顺风耳”。
然而,这样的“好日子”持续时间并不长。国民党方面很快就察觉到了异常,并迅速开始启用密码进行通讯。这一转变,无疑给红军的侦听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,前线指战员常常因情报缺失而陷入被动,甚至导致惨重损失。面对严峻挑战,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高瞻远瞩,痛下决心。
他们果断决定,集中红军内部最优秀的无线电技术人才和所有可能获得的设备,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破译国民党密电的部门——“中央军委第二局”,简称“二局”。这个部门对外极度保密,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。首任局长曾圣希(又名曾希圣),便是这支看不见的队伍的领军人物。
二局的诞生,标志着红军情报侦察工作迈入了专业化、体系化的新阶段。他们不再是靠着缴获的设备随意监听,而是有组织、有计划地进行高强度破译。从最初的“半部电台”监听,发展成为能洞悉敌情的“千里眼顺风耳”,这其中凝聚了无数无名英雄的智慧与心血。
二局的成立绝非纸上谈兵,它在战场上迅速展现了非凡的价值。在曾圣希的带领下,二局的精英们夜以继日,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,对海量的国民党密电进行筛选、分析和实验。那些枯燥的数字、繁复的符号,在他们眼中,都变成了敌军行动的蛛丝马迹。
他们陆续攻克了“壮密”、“展密”、“猛密”等多部国民党重要密码。尽管国民党为了防止泄密,也经常更换更高等级的密码,但在红军二局面前,这些努力往往只是徒劳。敌人在暗中变换着招数,却不知道,自己的底牌早已被人看得清清楚楚。

1933年3月,蒋介石命令陈诚指挥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“围剿”,企图通过多路大军对红军实施“分进合击”。然而,二局及时破译了敌军密码,侦听到敌52、59师的准确动向:他们正准备从乐安出发,前往黄陂与罗卓英的11师汇合,继而向广昌、宁都靠拢,意图切断红军退路。
这份关键情报,让中央军委得以提前部署,决定对国民党52、59师发动伏击。最终,在登仙桥一带,红军将这两个师全歼,取得了第四次反“围剿”的重大胜利。文章开头那位李默庵所率的第10师,正是跟进部队,才侥幸逃过一劫。当他抵达登仙桥时,映入眼帘的是漫山遍野的国军尸体。
悲怆之情涌上心头,他提笔写下了那句“登仙桥畔登仙去,多少红颜泪始干。”为了防范蒋介石猜忌,特意以密电形式发给了远在上海的夫人,却不料被二局截获破译,成为红军情报能力的一个生动注脚。蒋介石却对此浑然不觉,仍固执地认为红军获得情报是由于“人为疏忽”,一味强调“忠诚”。这种信息的不对称,注定了国民党在对决中常常处于劣势。
二局在后来的长征中,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,甚至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为“如果没有二局,红军的长征是不可想象的!”这句话,分量何其之重。长征,那是一段在死亡边缘徘徊的史诗,每一步都踏在刀尖上,稍有不慎,便是万劫不复。
例如,在著名的通道转兵会议上,正是凭借二局侦获的国民党企图在湘西“围剿”红军的准确情报,毛泽东据理力争,说服了中央改变行军路线,使红军转危为安。如果没有这份及时的情报,红军很可能陷入重围,长征的命运也许就此改写。
在“四渡赤水”这样极富传奇色彩的战役中,二局的情报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,帮助毛泽东掌握敌军动向,为红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,实现了战略主动。毛泽东曾形象地称赞二局的工作,将其比作“玻璃杯里押宝”,意指对敌情了然于胸,赢得胜利水到渠成。他还曾说,红军长征就像“打着灯笼走夜路”,而这“灯笼”无疑就是二局提供的情报之光。
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,情报工作不再仅仅是战场上的破译,更是上升到与公开斗争相统一的战略层面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中共中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,进一步提出了“隐蔽精干、长期埋伏、积蓄力量、等待时机”的地下斗争方针。毛泽东明确指出,为了消灭敌人,必须要有“两种战争:一种是公开战争,一种是隐蔽战争”,从而奠定了隐蔽斗争的军事地位。

为了更好地组织和领导这项工作,1939年2月,中共中央在延安组建了中央社会部,专门培养党的地下工作人员,让他们掌握秘密工作纪律和技术。毛泽东还强调“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”,成立了中央研究局和材料室,专门搜集国内外情报。据传,日本《朝日新闻》在日本出版仅10天,便能出现在延安的办公桌上,其速度之快令当时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都感到震惊。
这不仅是技术和组织能力的体现,更是对情报价值高度重视的明证。在隐蔽战线上,无数无名英雄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,为党和人民提供了关键情报,化解了多次重大危机。他们的名字不被知晓,他们的事迹鲜为人传,但他们却是人民最坚实的盾牌。
1943年,蒋介石蓄意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,密令胡宗南部闪击延安。然而,隐蔽在胡宗南部担任机要秘书的熊向晖,提前预警并及时将作战计划报告给党中央。毛泽东立即采取应对措施,不仅致电白区各界揭露阴谋,还向全国发出通电,挫败了蒋介石进军陕北的企图。
同样在解放战争后期,1948年蒋介石命令傅作义进攻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和石家庄。毛泽东通过隐蔽战线获得了详尽的作战计划,不仅提前部署,更创新性地运用舆论“攻心战”,通过新华社广播多次揭露敌人的偷袭阴谋,争取了民众支持,瓦解了敌军士气。最终,蒋介石的计划彻底破产。
随着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城市,毛泽东提出,城市地下工作不能单纯隐蔽,更要“联系群众,主动出击”,让精干的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隐藏在广大群众之中,并通过“改名换姓”等灵活方式,建立新的可靠据点。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,党的隐蔽力量得以壮大,为和平解放北平、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、保护城市有生力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毛泽东曾高度评价:“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。”这句话,是对无数情报战线无名英雄的最高褒奖。从红军早期依靠“半部电台”的艰难起步,到建立专业化的“二局”,再到将隐蔽斗争上升为与公开斗争并驾齐驱的战略支柱,中共的情报工作始终走在时代前列。它不仅是战场上的“千里眼顺风耳”,更是战略布局中的“玻璃杯”,洞察秋毫,决胜千里。这场看不见的战争,虽然没有枪林弹雨的壮烈,却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智慧较量。虽然没有勋章奖章的荣耀,却铸就了共和国的坚实基石。那些隐姓埋名、出生入死的隐蔽战线英雄们,他们的事迹或许不为人熟知,但他们筑起的,是一座座看不见的丰碑,永远屹立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。
长宏网-成都配资网-炒股配资服务-配资公司app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